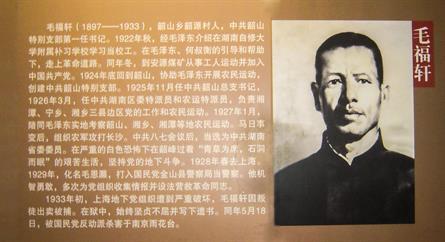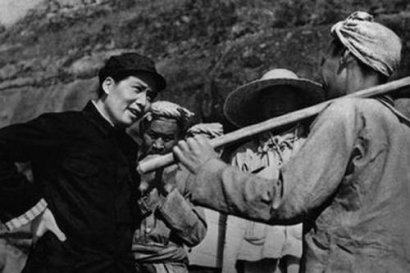留得青白在人间——记张培之烈士
更新时间:2022-12-24 11:30:08点击:
留得青白在人间
——记张培之烈士
任孝廉
1940年4月里的一天下午,乐陵官道刘日伪据点通往村东刑场的路上三步一哨,五步一岗,敌人骑兵队巡逻往返。鬼子小队长久寒丘身佩长刀临阵指挥,将3个五花大绑的青年人押向那里。其中一个人伤势严重,步履艰难,但他用力挣脱了敌人的拖拽,昂首挺胸,坦然地走向刑场。他,就是冀鲁边区三地委秘书长张培之。
张培之,又名张栽云,化名李杰。1907年出生于山东省沾化县泊头乡官庄。幼年时期,家里单靠有病的父亲养活不了全家5张嘴,经常靠借贷过日子。刚记事的张培之眼巴巴看着大人背进一斗粮食偿还二斗半,对此他困惑不解。万恶的旧社会给张培之幼小的心灵印下了深深的阶级剥削的烙印。
1926年8月,靠外祖父家供济,张培之入惠民岱北公学学习。随着视野的扩大,他看到帝国主义列强纷纷侵略中国,强烈的民族荣辱感在心头滋生,便努力探索救国救民的道理。在他翻阅了《孙中山全集》、《建国方略》等大量书籍之后,他逐步摆脱了封建思想的束缚,开始接受新的思想,主张民主政治,改革社会,向农民宣传“耕者有其田”的主张。
1929年夏,张培之考入被誉为“红二师”的曲阜第二师范求学。当时校内进步思想活跃,要求政治民主的呼声甚高。为了反对蒋介石来孔庙祭孔时所散布的尊孔邪说,革命师生上演了讽刺剧《子见南子》,这在中国学生反帝反封建运动史上留下了值得记载的一页。张培之就是震惊中外的“子见南子案”参与者之一。
1930年,张郁光来校任校长。他提倡普罗文学,并主张学习社会科学,扩大图书馆,购置马列经典著作。张培之先后读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唯物辩证论》等马列著作,从而认识到“只有马列主义才能救中国”的这一真理。
1931年7月,张培之由曲师毕业回沾化。先后在泊头二高和黄升小学任小学教师。在这期间,他坚持通读了《资本论》,经常做社会调查,了解穷人疾苦,宣传破除迷信等进步思想。他经常与进步人士一起说古论今,抨击时弊,抒发自己的抱负,有时又独坐家中对灯长叹。有一次,小妹妹不解地问:“哥哥,你常年在外教书,家里的事又一点不管,整天唉声叹气,你到底愁个啥?”张培之稍顿了一下,耐心地说:“好妹妹,哥哥愁啥,不能告诉你。我所愁的是件很大很大的事,等你长大了就知道了。”
1935年初,为寻找党组织,张培之离开家乡到商河县龙桑寺乡农学校教书。此时,日本帝国主义继“九·一八”之后,进一步向华北地区发动新的进攻。国民党政府继续执行卖国政策,并集中力量攻击北上抗日的红军,镇压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日本帝国主义的加紧侵略与蒋介石奉行卖国内战政策,构成了中华民族的空前危机,张培之的心情十分沉重。当时商河地处华北交通要道,敌、顽聚结,派系复杂,党的活动尚未开展,国民党反动派一统天下。在学校,张培之身居异域之中,胸中抱负难以施展,压抑感更加沉重。1936年12月的一天中午,张培之正在教室演奏风琴,以解被压抑得几乎承受不了的苦闷心情的时候,报纸传来“西安事
变”的消息。张培之阅后拍案而起,一股狂喜的心情使他再也按捺不住,拍掌连连叫“好”。国家与民族的危亡,使张培之再也沉沦不下去了,于1937年初,毅然辞去教师职务,返回家乡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寻找共产党。他借走亲访友之机,在邻庄亲朋、同学之间奔走,宣传鼓动“誓死不当亡国奴”,带头抵制日货。抗日的星星之火,在沾化大地蔓延开来。
1937年9月,沾化有了党的活动,张培之的同学石清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年冬,经石介绍,张培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沾化县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从此,他协助石清玉于1938年春建立了“抗日救国读书会”,广泛团结知识分子,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同时向会员指出:“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并从他们中间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党的组织。这年4月,张培之巧妙地把“读书会”扩办到国民党刘景良部的政训处里,从中秘密发展王瑞锋等先进分子入党,变国民党的政训处为我共产党八路军宣传抗日的阵地。
1938年秋,中共沾化县工委成立。石清玉为书记,张培之任组织委员。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党的工作应寓于职业之中”的指示,县工委在井王村设小学一处,由张培之任教员,负责党的联络工作,恰在沾化建立抗日民主统一战线,他经常接近国民党进步人士隆梦华,做细致的工作,使隆茅塞顿开,支持抗战。
同年底,张培之到朱鄢隆梦华家做争取赵玉的工作,恰与同学国民党顽固派吴克廷相遇了。吴克廷挑衅地当着张培之面讲共产党的坏话。张培之顿时火冒三丈,拍案而起,震得桌上的壶碗一起作响,他用国民党反动派奉行卖国内战政策,对日不战,对内制造磨擦的事实怒斥吴克廷的诽谤,使吴克廷无言可答,悻悻溜走。
1939年秋,冀鲁边区重建鲁北地委时,组织上调张培之任鲁北地委秘书长,兼管党员教育工作。此时他化名李杰,经常代替地委起草文件,代表地委答复、处理各县党组织的公函。他率领地委机关活动于商河、阳信、乐陵三县边境一带。张培之以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中艰苦奋斗的事例教育大家,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次,地委由王道然庄转移到大韩庄。3天后,张培之发现临走时有一户群众没收粮款,他亲自跑了7、8里路把款送去。
1939年,地处华北平原的我鲁北抗日根据地经常受到敌人频繁而残酷的扫荡袭击。日、伪、顽勾结,实行“三光政策”,制造白色恐怖,全国抗战处于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及时作出了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和教育工作的指示,鲁北地委迅速开展了党员培训工作。张培之兼任党训班的主持人和授课人。他要求每一个党员要经得起恶劣环境的严峻考验,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增强党性,时刻准备吃苦,坚持抗战到底。他要求每一个党员要保持革命气节,无愧为一个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为避免暴露,党训班经常变换开班地点。是年冬,地委机关驻五大店,敌人向这一带扫荡。张培之立即分头通知机关人员赶快转移。当撤离村子半里路远的时候,张培之突然发现自己未穿外衣。他想起衣袋里的文件,说了声“糟糕”,回头就向村子跑去。当他取回衣服刚刚跑出村子时,敌人就冲进了村庄。
1940年2月,张培之冒着严寒带公务员到乐陵五区花园街东张家店办党训班。由于汉奸伪村长张同升告密,张培之不幸被官道刘据点的日伪军逮捕。敌人将他间另外两个刚报到的学员一起押回据点,关进严密看守的伪警备队监狱。
在监狱里,张培之冷静地分析了目前的处境,意识到一场严酷的斗争摆在大家面前。对党员进行严守秘密、保持革命气节的教育,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他秘密召集大家,严肃地说:“同志们,党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在敌人面前,我们每人的表现如何,就是鉴定我们党训班学习成绩的最好答卷。现在,我来开讲党训班第一课:严守党的秘密……”
翌日,审讯在伪警备队大院开始。堂上一片阴森,如狼似虎的汉奸分列两旁,地上放着各种刑具。
汉奸刘聚轩冷冷地问:“你就是共产党地委秘书长李杰吗?”
“你既然知道,何必再问!”张培之的回答,使刘聚轩碰了一鼻子灰。他悻悻地来回走了几步,翘着大拇指说:“痛快,敢做敢当,痛快!”
“将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将那些吃里扒外的狗杂种斩尽杀绝,那才是真正的痛快!”张培之坦率的回答击中了汉奸走狗的痛处,气得刘聚轩咬牙切齿,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你——你不要忘了你站在什么地方!”
“我乃堂堂中国人,站在中华民族的国土上!”张培之义正辞严地答道。
“可眼前你是我的阶下囚,你们的生死簿握在我的手心里。”刘聚轩狞笑了一声,接着把话一转,诱惑地说:“不过,只要你说出你们的地委和区委哪里去了,我可以保你无事……”
“要我说出来倒也容易。”
“怎么样?”刘聚轩喜上眉梢,急迫地追问。
“那要等中华民族彻底解放,你们这些鬼子汉奸死绝之日!”
刘聚轩像只红了眼的疯狗,暴跳如雷,跺着脚嗷嗷狂叫:“给我打!往死里打!”匪徒们捆了培之的双手,把他吊在梁上,几支蘸了水的皮鞭没头没脸地在张培之身上乱抽。
“快讲!地委机关在哪里?”
张培之脸上鲜血混杂着豆大的汗珠往下滴,眼里放射着坚毅的光:“地委机关在我的脑子里,在我的胸膛中!”
刘聚轩恼羞成怒,手指着各种刑具凶残地说:“我叫你尝遍这些刑具的滋味!来呀……”几个打手蜂拥而上。
张培之被敌人用烙铁烙,压杠压、辣椒水灌……
敌人用尽了招数,把张培之折磨得死去活来,伤痕累累,肋骨折断好几根,但他始终守口如瓶,没向敌人透露半点我党机密。
张培之的英勇表现,为另外几个同志做出了光辉的榜样,用实际行动给狱中党员上了一堂生动的党课。他们在敌人的审讯中也都坚贞不屈。每次受审回来,张培之挣扎着,去抚摸同志们的伤处,询问疼不疼,并用明朝的一首《咏石灰》诗勉励大家: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身碎骨都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张培之向大家讲人生的价值意义,教育大家学习石灰的风格,树立“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革命人生观。告诫大家莫愧为一个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
敌人妄图彻底破坏我地委党组织的梦想破灭了,张培之机警地意识到斗争已到了最后的时刻。他根据几天来的观察,秘密召集大家决定在最后的时刻做最后的斗争,抓紧时机,越狱出去,不成功便成仁。
张培之摸清了敌人的岗哨布置情况和活动规律,密选伪警备队东墙下大水沟为突破点。一天清晨,张培之趁敌夜哨与白哨换岗的机会,发出行动的命令:“争取生存的最后时刻到了,按原定地点越狱。你们先逃,我来断后。”同志们扛开监狱的木门,顺墙根向北悄悄摸去。水沟很窄,勉强能钻出一个人,刚一露面,就被敌人发觉了。顿时枪声密集,喊声嘈杂响成一片,逃出的同志很快被迫截回来。
越狱未成,敌人使出了最后的手段。当天下午3点钟,张培之等同志被押赴刑场,他们在敌人的枪口之下面不改色心不跳,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日寇必败,中国必胜!”、“中华民族解放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张培之从容就义了。在人类历史的长河里,他仅度过了短暂的33个春秋。然而,在这极其短暂的一生中,他致力于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为冀鲁边地方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呕心沥血,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