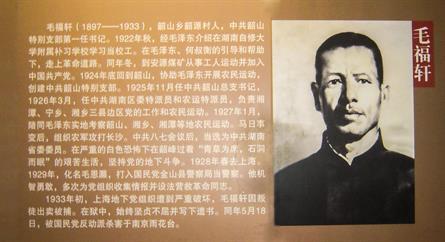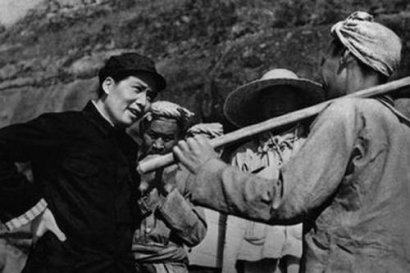夏云超烈士传略
更新时间:2022-11-06 11:30:01点击:
夏云超烈士传略
张思衍 王可鹏 岳昌锁 王海田
夏云超,原名夏元峋,山东省荣成市桥头镇观里夏家村人,1917年出生于一个地主家庭。兄弟七人,他排行居五。幼年时父母相继去世,他跟随当医生的长兄夏岳五长大成人。夏云超自幼聪敏,勤学好思,举止稳重。在邻村风山小学毕业后,大哥又先后资助他去威海金泉顶中学和北平宏达高级中学读书。受大哥从医的影响,他于1934年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读书。
夏云超的青少年时代,正是军阀混战,强梁横行的年月。他虽出身富家,但在学校里长期与同学中平民百姓家的孩子接触,耳闻目睹民间疾苦,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踏向东北、华北大地,广大人民群众身受双重压迫,生灵涂炭,苦不堪言的悲惨情景,唤起了夏云超强烈的忧国忧民之心。他在寻求真理的道路上,受《新青年》《向导》等进步书刊的影响,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特别是经过“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的战斗洗礼,更使他的思想产生了一个飞跃。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侵略华北,并收买汉奸,积极策划“华北防共自治运动”,妄图吞并华北,进而达到独霸全中国之目的。亡国的阴霾笼罩着祖国半壁河山。12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北平近万名爱国学生从各个大学冲出来,走上街头,进行抗日救国大请愿。他们冒着凛冽的寒风,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正在北大读书的夏云超也满怀一腔热血,义无反顾地加入浩浩荡荡的示威游行队伍的行列。队伍到达王府井大街时,遭到国民党武装军警的镇压,当场有百余名学生受伤,30余人被捕。面对反动派的暴行,夏云超没有被吓倒而是更加积极地投身于这场革命的洪流。第二天北平各学校学生实行总罢课。夏云超和同学们一起,走上街头,发表演讲,揭露国民党反动当局的卖国罪行。12月16日,夏云超又挺身参加了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反对成立所谓“冀察政务委员会。”游行示威得到了全国各地学生的支持和响应,从而在全国掀起了一个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
在这场汹涌澎湃的学生爱国运动中,夏云超经受了革命斗争的锻炼,激发出极大的爱国热忱。此后,他又积极参加了我党领导的学生联合会,同反动分子组成的“新学联”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还参加过声援爱国进步人士“七君子”的活动。“七·七”事变爆发后,平津相继沦陷。北平各校被迫停课,纷纷南迁。夏云超参加了平津流亡同学会,与同学们一起来到济南。后因在济南生活无保障,夏云超辗转回到老家荣成,住在城厢大哥夏岳五家里。
荣成是胶东地区共产党组织建立较早的县份之一。早在1932年,党就在这里撒下了革命的火种。夏岳五在城厢开设了所“崇德药房”。他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抗战初期,就与中共城厢支部负责人曹漫之、李耀文交往密切。夏云超经大哥介绍,很快结识了曹、李二人,并将自己回乡参加抗日救亡的想法和决心向他们作了汇报。曹漫之、李耀文非常赏识这位从高等学府回来的爱国学生,吸收他参加了“河山话剧社”。剧社分设戏剧队宣传队和歌咏队。夏云超经常随同剧社下乡进行宣传演唱。每到一地,他既教唱《抗日进行曲》等革命歌曲,又登台宣传我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对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抗日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938年春节过后,夏云超经人介绍到窑上村小学任教。在课堂上他向学生讲述“九·一八”、“一二·九”等重大历史事件,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他还积极参加油印传单、张贴标语和传递情报等革命活动。
同年4月,在李耀文等人的推荐下,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决定抽调夏云超到部队当军医。党的需要是革命者的志愿,夏云超欣然接受党的调遣,脱下长衫,兴冲冲地踏上了军旅之途。
到部队后,夏云超多次亲临战场,冒着战火勇敢抢救和运送伤员,屡受部队首长的表彰。同年5月,三军改编后,他担任三军三路卫生处主任。当时的卫生处缺医少药。面对战斗频繁,伤员日趋增多的情况,夏云超想方设法解决困难。他到处求亲托友采购药品和医疗器械,重伤员和病号就送到他大哥处治疗。当第一次把一位重伤员连夜送到大哥家里时,他抱歉地对大哥说:“你看,我事先没和您商量,就把伤员抬来了…”夏岳五没等他说完,就诚恳地说:“你这是说的什么话,你不送到我这里,还能送到哪里呢?”夏岳五当即把自己的房屋腾出来作临时病房,无偿地收治伤病员。前前后后共为三军治愈伤病员10余名。
1938年9月,三军总部在掖县沙河镇与三支队合编,成立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五支队(简称五支队)。下辖4个团。夏云超调往六十一团任卫生队长,并在此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0月中旬,我军攻下掖县的杜家围子后,部队开往平度城北的大青扬休整,准备攻打平度城。15日拂晓,与日伪军遭遇。战斗一直持续到日落西山,共毙伤敌人230余人。战斗打得非常艰苦,我军伤亡也很重。夏云超忙前跑后组织抢救和转移伤员。重伤员刘琪肺部被打穿,躺不下,坐不住,伤口还不时流血,脸色一会儿蜡黄,一会儿潮红,异常痛苦。夏云超想到必须采取适当的卧位,才能减轻痛苦,利于呼吸。于是他迅速跑到群众家找来个驮篓,垫上棉被,将刘琪放在里面,夏云超靠在身边扶着他。连日的行军、抢救,夏云超十分疲惫,他多想美美地睡上一觉。可为了减轻战友的痛苦,他佝偻着身子,咬紧牙关坚持着,甚至不敢轻轻地动一动。时间好像凝固了,夜是那样的漫长。夏云超周身酸痛、僵麻,但听到刘琪的呻吟声渐渐低下去,呼吸顺畅了些,他心中说不出的欣慰。天刚放亮,他就马上派人送刘琪到掖县城治疗。
不久,五支队在黄县文基大姜家村成立起胶东抗日部队第一个后方医院(以后为适应战时需要,总院不断扩大,下设若干卫生所),夏云超被任命为院长。这年冬,夏云超与共产党员、卫生员宁超结成革命伴侣。
创办“后方医院”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当时的医院,药品器械极少,更没有一个正规的专科医生。护士百分之七八十是农村妇女,年龄都在十五六岁,大的也不过20岁左右,根本没有受过专门训练。面对这些困难,夏云超不但没被压倒,反而激发出极大的革命热情。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夏云超决定以培养政治坚定、技术优良的医护人员为宗旨,对各所进行轮训。整个培训工作全由他一人承担,又当院长,又当教员,一身二任,总是在不知疲倦地工作着,晚上编写教材常常通宵达旦,彻夜不眠,白天还要照常讲课。在教学内容上土洋结合,增加了按摩和平时搜集的民间土方验方。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时间抓得很紧,每天要求学员学足9个小时。傍晚,他还领着学员帮助驻地群众劳动,培养同志们的群众观念。他待人诚恳,平易近人,没有架子,循循善诱,诲人不倦,手把手地传授技术,是医护人员的良师益友。
在培训中,夏云超还特别重视理论联系实际,让学员们在战争中服务,在服务中学习。在一次战斗中,夏云超和卫生所的领导共同组织医护人员抢救和运送伤员。战后,他联系战斗实际讲课。既讲述战地救护常识和实践经验,又突出地进行“有我们在就有伤员在”的革命英雄主义教育。这种教学方法,学以致用,使学员的思想和学业进步很快。
经过半年多的时间,夏云超把各所医护人员轮训了一遍,为提高全院医护人员的政治、业务素质做出了贡献。
同时,夏云超还经常深入到驻地老百姓家中访贫问苦、看病治病,很受群众的尊敬和爱戴。当地群众都说:“八路军五支队出了一个好名医。”
由于战斗频繁,部队流动性很大,后方医院也经常搬迁。每次转移,从轻重伤员的编队,到具体的负责人员,夏云超都一一落实,亲自过问。在路上,他跑前跑后,生怕有一人掉队。当大家都休息时,他还在油灯下学习文件或研究治疗方案。他的行动不是号召,胜似号召;不是命令,赛过命令,有力地激励带动着全体工作人员。当时医院虽然人手不多,但都能积极主动地工作,想方设法克服设备简陋的困难。就这样,后方医院在艰苦的条件下,较好地担负起了伤员的治疗任务。
夏云超还善于团结群众。不论是来自何地,有过什么经历的人,只要是为革命工作走到了一起,他都看成是一家人,给以充分的支持和信任,放手让他们大胆工作。医院里有一位邵医生,家住掖县敌占区,是被顽军张金铭部强拉去当军医的,在平度孙镇战斗中被我军解放过来。此人有抗日救国的愿望,也有一定的医疗技术,经教育愿意留下来工作。但他受不了艰苦生活的磨炼,有时发几句牢骚,闹点情绪,有些同志看不起他。夏云超了解情况后,经常主动接近他和他一起研究工作,关心他的生活,鼓励他大胆工作。有一次邵医生负责治疗的伤员中,有几人伤口感染化脓,不少人对此议论纷纷。夏云超说:“工作中难免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谁都不能保证自己万无一失。我们要相信同志……”他积极和邵医生一道抢救伤员,有效地抑制了伤员的感染。邵医生很受感动。在以后的工作中,他任劳任怨,积极肯干,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在一次反“扫荡”战斗中,他因掩护伤员而英勇牺牲。
一次,从前线送下来一位王连长,伤势很重。因得不到及时治疗,伤口恶化。夏云超在检查伤情时,发现有蛆从他腿上的伤口里往外爬。夏云超轻轻地为王连长清洗伤口,一面细心观察他的表情。王连长看出他的意思,咬牙说道:“不要管我疼不疼,你大胆地治。早治好伤,我好早上前线。”夏云超听后心情激动,他对身边的医护人员说:“我们党有这样的好干部,事业定会成功!”为了使王连长早日康复,他一连几天不回家,日夜守护在他的身旁。院里的医生去替他,他说:“大家忙了一天,都回去休息吧,我来值班。”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治疗和护理,王连长的伤情大有好转,夏云超日见憔悴的脸上也露出了笑容。
1942年是胶东人民抗战史上最为艰苦的一年。日寇为保证东北至山东的海上运输畅通,支援太平洋战争,加紧与胶东的各顽固派勾结,疯狂“扫荡”,妄图摧毁我抗日根据地。7月1日,山东纵队第五支队奉上级指示撤销,成立胶东军区,夏云超调任军区卫生处长兼政委。面对险恶的形势,他更加忘我地工作。他深入西海、南海各分所和连队调查,写出调查报告,建议连队要配有卫生员,营里要有医生负责的包扎所,各团设分所,各军分区要成立后方医院,并提出以团为单位培训卫生员,医护人员要下放充实基层力量,对伤病员要采取分片医治的办法。他的这些建议,受到军区党委的赞扬和肯定。
这时期,夏云超为部队的医务卫生工作倾注了满腔心血,做了大量工作。他一向把政治工作视为部队卫生工作的生命线,利用战斗间隙,常组织卫生干部、战士结合战争实际,学习马列理论,上级指示和时事政策,并且经常和同志们促膝谈心,做思想工作,提高同志们的思想觉悟,鼓励同志们树立战胜困难的勇气。他还善于听取群众意见,正确处理同志间的分歧意见,并能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有一次,他对一位战士发了脾气,说了一些粗话。当天晚上回到家里心里总是不安。他对妻子说:“那个同志平时一贯积极,偶尔出现点问题我为什么要发火呢?这样是会挫伤他的积极性的,真不该呀!”第二天一大早,他便找到这位同志,给他赔礼道歉,求得谅解。由于夏云超善于做政治工作,民主作风又好,因而使全处上下形成了和谐、团结、积极向上的政治气氛。
夏云超是一个不怕艰苦,严谨扎实,注重实际的人。战时他同卫生处的同志们一起救伤员,抬担架,并在斗争中鼓励同志们克服眼前的困难,努力做好工作,去迎接新的胜利。哪里困难大,哪里有危险,他便到哪里去。凡是他到过的地方,同志们都受到他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感染和鼓舞。平时,他总是以身作则,多办实事。当时环境艰苦,病房分散在各村各户。为了掌握基层情况,他经常走村串户查看病房。
夏云超是高级知识分子,又是领导干部,本应享受较高的生活待遇。但他的生活一贯俭朴,克己奉公,对自己要求很严格。他拒绝吃小灶,和战士一样吃派饭,吃饼子,喝地瓜汤。一次他感冒了,炊事员特地给他做了一碗鸡蛋汤,他说什么也不喝,说:“在这艰苦的战争年代,大家要同甘苦共患难。我是共产党员,哪能闹特殊呢。”他有马,但移防时一般自己不骑,不是让给体弱有病的同志骑,就是用来驮文件、书报、灶具等。同志们常常亲切地挑着大拇指说:“咱们的夏处长真是好样的!”
1942年11月初,日寇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亲率两万日伪军,对胶东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拉网扫荡”,形势非常严峻。为了保证部队伤病员的安全,卫生处奉命在日寇扫荡之前,对已疏散到各地的伤病员进行一次大检查。于是夏云超风尘仆仆地来到马石山地区驻有伤病员的村庄(现属乳山县),检查伤病员的生活、治疗和备战设施情况,并帮助解决具体问题,提出今后工作的改进意见。工作将告结束时,他来到疏散在上杨家村的妻子宁超身旁。这时,妻子已经生下了一个女儿。他抱着女儿,边亲吻边问妻子:“你知道咱女儿为什么这时来报到?”没等妻子回答,他接着幽默地说:“她是来参加反‘扫荡’啊!”两人都笑了起来。宁超让丈夫给女儿起个名字,夏云超思索了一下说“对这次反‘扫荡’,我们要英勇战斗,去争取胜利!‘英勇加胜利’,就是咱女儿的名字,叫英利吧。”充分表达了他对这次反“扫荡”的战斗决心和胜利信心。
夏云超在家里只住了一天,因为还有许多工作等着他去做。握别时,夫妻互相激励在反“扫荡”中再立新功。
夏云超离开妻子的第二天,也就是11月23日,日寇突然将包围圈缩紧到马石山地区,把几万名干部群众包围在方圆不足40里的圈子里。这时,夏云超因工作原因没能离开此地,也被包围了。11月24日,日寇枪杀了我军民500多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马石山惨案”。夏云超就在这次惨案中,带领群众突围时,不幸中弹,光荣牺牲,年仅25岁。
“壮志未酬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夏云超是胶东军区卫生工作的创建者之一,他的牺牲,是胶东医务工作的重大损失。他的英名刻在“马石山殉难军民纪念碑”上,也铭刻在千百万胶东人民的心里。